世界正在轉向可再生能源
全球能源體系似乎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顯然在轉向可再生能源,同時減輕對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依賴。
如今是能源行業的奇特歲月。該行業正在涌現一些令人吃驚的頭條新聞,這些新聞在短短幾年前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5月,迪拜水電局(Dubai Electricity and Water Authority)表示,其已收到幾份開發太陽能發電項目的計劃,完工后的電力批發價格將低于每千瓦時3美分。這創下了全球向電網輸送太陽能電力的合同價新低,且遠遠低于這個酋長國和其他國家通常向燃煤電廠購買電力的基準價格。
在以悲催的陰天聞名的英國,今年5月太陽能電池板向電網輸送的電力高于燃煤電廠。
在能源需求極大的洛杉磯,美國愛依斯電力(AES)正在安裝世界上最大的電池,其可在需求高峰為數十萬家庭供電,取代那些隨時待命對電網增加供電的燃氣電廠。
世界上最大太陽能電池板生產企業、中國的天合光能(Trina Solar)表示,去年開始向20個新市場銷售產品,從波蘭到毛里求斯,從尼泊爾到烏拉圭。
拋出這等非凡新聞的并非只有可再生能源。咨詢公司Wood Mackenzie表示,過去兩年里,美國頁巖油田的生產成本已削減40%之多。近期,裝載液化天然氣的貨船從美國駛往海灣,將北美的過剩產量供應給迪拜和科威特市場,盡管這兩者地處世界最大油氣產區之內。
這些故事的意義在于暗示,全球能源體系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行業內的公認智慧正受到挑戰。顯然,世界正轉向可再生能源,同時——從占消費總量的比例看——減輕對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依賴。
在化石燃料市場內部,有些燃料(比如天然氣)正變得比其他燃料(比如煤炭)更受歡迎。政策制定者和行業專家心里的疑問在于,這些變化可能走得多遠?發生速度有多快?
幾十年來,對能源領域的最新趨勢抱懷疑態度總體上是明智的。油田和電廠等資產是大筆投資,其運行壽命可以持續好幾十年,所以燃料結構和發電資產的改變是緩慢的。
6月,BP首席經濟學家斯賓塞•戴爾(Spencer Dale)發表了一張很有意思的圖表,顯示現有能源和技術的普及速度,清楚表明這往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例如,在1899年,天然氣僅僅滿足了1%的世界一次能源需求。50年后,這個比例上升至8%。
盡管可再生能源近年增長迅速,但其基數非常低。BP數據顯示,去年,“現代可再生能源”——主要是生物燃料、風能和太陽能,但不包括水力或傳統的生物質——僅僅滿足了2.5%的世界一次能源需求。
話雖如此,歷史上也不乏能源體系在達到拐點后發生迅速變化的例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石油消費量一直穩步增長,但在一戰期間和之后才真正起飛,因為戰艦從煤炭轉向燃油,而陸軍借助汽油和柴油發動機車輛實現了機械化。
1973年阿拉伯世界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以及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后,核電出現了相似的飛躍。
如今,政府為應對氣候變化威脅而出臺的政策,成了推動能源體系發生變化的因素。
在去年底的巴黎氣候談判中,195個國家做出了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這表明,無論這個問題在美國可能引起多么大的政治爭議,全球范圍的壓力不太可能很快消失。
這個特別報道系列介紹了幾種創新技術,它們有望給能源行業部分領域帶來進一步變化。例如,有人提議到2025年就可在美國或英國投入運行的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堆,它們有助于避免大型反應堆的巨大成本。
與此同時,化石燃料公司在維持自身競爭力方面也在取得進步。這并非易事。不僅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在過去兩年里大跌,而且從長遠看,需求預計會變弱,而供應會更加充足。該行業公司的估值已受到嚴重擠壓。
另一方面,有些新能源技術并未取得太大進展,比如能夠捕捉并存儲自己所排放二氧化碳的發電廠。政策制定者們普遍認為,如果人類打算繼續享受化石燃料的好處、同時避免其污染效果的話,碳捕捉已變得必不可少。
另外,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的發展軌跡顯然將不會是一條直線。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數據顯示,自2015年創下最高紀錄以來,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今年已失去勢頭。2016年上半年,清潔能源投資同比下降23%。
即便如此,一場相當突然且影響深遠的能源轉型的各項元素正在陸續到位,其觸發因素可能是出乎意料的油價持續大漲。如果中國或印度對電動汽車做出大規模政策承諾,那將對石油需求前景產生戲劇性沖擊。
在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旭日東升》(The Sun Also Rises)中,有個人物說,他是以兩種方式破產的,“先是逐漸,接著突然。”在我們的能源體系中,一場深刻的轉型有可能以同樣方式悄悄向我們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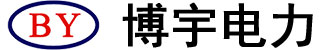
 采購:15308655582
采購:15308655582 
